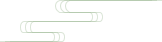
孔子一个孤独而自由的追梦人
今天,我要和大家谈的话题是“孔子:一个孤独而自由的追梦人”。关于孤独,我最近有一个比较深的感受,那就是人人都要经历孤独,无论是荣耀在身万众瞩目的还是普普通通孑然一身的,都要面临孤独的时刻,遭受挫败时、独对难题时,这些都是孤独时分,不是此刻孤独,就是彼时孤独,只不过每个人孤独的程度不同而已。在孤独这件事上,每个人都不孤独,每个人都一样。所以,如何面对孤独,如何与孤独相处,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。
我在读《论语》时,感觉到孔子是一个很丰富的人,是一个能够多角度解读的人物。而他的孤独,也是其中一个很鲜明的特征,所以,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孔子的孤独。
孔子在今天的社会得到了很高的赞誉,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备受关注,孔子被誉为“世界十大名人之首”,美国最高法院的门上就刻有孔子的雕像,孔子学院遍布全球各地。
但是,在遥远的春秋时代,孔子并没有今天的光华,他生前坎坷,颠沛流离,特别是晚年的时光,亲朋离逝,凄凉孤独。
孔子68岁时回到鲁国,才过一年,他的儿子孔鲤去世了;71岁时,绝笔《春秋》,他最爱的弟子颜回病逝;72岁时,和他有深厚感情的子路在卫国被人砍死。
人世苍凉,亲朋离逝,生死无情,孔子咀嚼着这份孤独,不知道有多么痛苦和忧伤。然而他也说了:“七十从心所欲,不逾矩”,孔子在晚年的时候,见证了他身边太多人的离逝,而自己也将近人生的终结,此时,离死亡很近,他反而获得了一种大解放,大自在,孤独着,也自由着。
这份自由来自于他对理想的痴心不改,来自于他发愤勤恳,来自于他充实而无悔的一生,他晚年回顾自己的这一辈子,说道:“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,七十而从心随欲,不逾矩。”
当他这样回顾时,他对自己这一生的活法应该是抱着无悔的态度的,尽管他终身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,但是他“求仁得仁”,他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了一生,此生无悔,自然能从容自由地面对人生最终的落幕,这就是一种大自在、大自由。
孔子的孤独不仅仅是晚年时的亲朋离逝,更在于他在为梦想奔走的路上所遭受的挫败。
孔子超凡入圣,超前于时代,很多思想到了今天也不过时,所以当时同时代的很多人都难以理解孔子。
《论语》中就提到当时一些的隐士不能理解孔子,隐士接舆嘲笑孔子德行衰败,隐士长沮、桀溺、丈人都不认可孔子,都嘲讽他在礼崩乐坏的社会里提倡仁政,实在是不切实际、荒唐至极。
孔子的弟子们一个个能力都挺厉害,有些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,以至于那些不懂孔子的人就认为孔子不如他的个别弟子,比如有人说孔子比不上子贡。
子贡确实也非常能干,在当时的外交上成就卓著,在各国享有一定的影响力,于是有一些人就认为子贡比他老师厉害。
《论语子张篇》里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:
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:“子贡贤于仲尼。”
子服景伯以告子贡。
子贡曰:“譬之宫墙,赐之墙也及肩,窥见室家之好。夫子之墙数仞,不得其门而入,不见宗庙之类,百官之富。得其门者或寡矣。夫子之云,不亦宜乎!”
翻译一下:
叔孙武叔在朝廷上对大夫们说:“子贡比仲尼更贤。”子服景伯把这一番话告诉了子贡。子贡说:“拿围墙来作比喻,我家的围墙只有齐肩高,老师家的围墙却有几仞高,如果找不到门进去,你就看不见里面宗庙的富丽堂皇,和房屋的绚丽多彩。能够找到门进去的人并不多。叔孙武叔那么讲,不也是很自然吗?”
子贡口才很好,他说得很形象,他把自己比作齐肩的矮墙,一般人在外面就可以看到里边的建筑,而把孔子比作高墙,在外面的人是无法看到里边的富丽堂皇的,所以就认为子贡比孔子还厉害,那是因为一般人理解不了孔子的高度。所谓“高处不胜寒”,说的就是道理。
不仅这些人不理解孔子,更要命的是当时的执政者也不理解孔子,更谈不上要重用他,用他的仁政思想来治理天下。
孔子在齐国,希望得到齐景公的重用,结果也是因为得不到理解而无法实现这个愿望。
《孔子世家》中记载:
景公向孔子问政,孔子说:“君君,臣臣,父父,子子。”景公听了很高兴,觉得孔子可以重用,于是就想尼溪这块地赐封给孔子。然而晏子并不看好孔子,他向齐景公进言:“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;倨傲自顺,不可以为下;崇丧遂哀,破产厚葬,不可以为俗;游说乞贷,不可以为国。自大贤之息,周室既衰,礼乐缺有闲。今孔子盛容饰,繁登降之礼,趋详之节,累世不能殚其学,当年不能究其礼。君欲用之以移齐俗,非所以先细民也。”
晏婴进言说:“这些儒者能言善辩不能用法度来规范;高傲自大自以为是,不能任用他们来教育百姓;崇尚丧礼尽情致哀,破费财产厚葬死人,不可将这形成习俗;四处游说乞求借贷,不可以此治理国家。自从圣君贤相相继去世,周朝王室衰落以后,礼乐残缺有很长时间了。如今孔子盛装打扮,繁琐地规定尊卑上下的礼仪、举手投足的节度,连续几代不能穷尽其中的学问,从幼到老不能学完他的礼乐。国君打算用这一套来改造齐国的习俗,恐怕不是引导小民的好办法。”
齐景公听了晏子的话,虽然对孔子还是很恭敬,但不再问有关礼的事。有一天,齐景公对孔子说:“按照季氏上卿的规格来待你,我不能做到。”于是就用介于鲁国季氏和孟氏之间的规格来接待孔子。齐国大夫企图谋害孔子,再加上齐景公又说了:“我老了,不能用你了。”孔子就上路离开齐国,返回鲁国。
齐景公原本对孔子的想法挺推崇的,但晏子的劝阻使齐景公改变了自己的想法,孔子也就失掉了践行理想的机会了。只得落寞地回了自己的国家。
孔子到了卫国,希望在那里能有大展拳脚的机会。卫灵公对于孔子倒是很优待,给他许以比较好的待遇。之所以优待孔子,主要是想从孔子这里得到了行军打仗方面的策略。所以,就有了《论语卫灵公》里的一段记载:
卫灵公“问陈”于孔子。孔子对曰:“俎豆之事,则尝闻之矣;军旅之事,未之学也。”明日遂行。
“陈”即“阵”,行兵布阵之意,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军事方面的问题,孔子一听,又是一个只关心打仗的国君,于是,没好气地说了:“祭祀、礼仪方面我就还听过,打仗的事,未曾学过。”孔子通晓六艺,博学多才,军旅之事也是懂得的,可是孔子主张以仁治天下,虽然他也知道战争是客观存在,不可避免的,但他希望国君更关心“仁政”的问题。显然,卫灵公对此毫无兴趣,孔子只得失望而去。
孔子自己感觉到了孤独,也曾感叹:知我者天乎!
这一句话是来自《论语 宪问篇》中的第三十五章:
内容如下:
子曰:莫我知也夫!子贡曰:何为其莫之子也?
子曰:不怨天,不尤人,下学而上达。知我者其天乎!
孔子说,没有人能够理解我。但是即使是这样,我也不怨天,不尤人。从身边附近的事物开始学习而晓达道义,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!
虽然孔子曾经说:“不患人不己知,患不知人也”。
但我认为孔子是在乎有没有人理解他的,因为他是个入世者,他要改革社会,需要别人特别是统治者的理解和支持。他曾说:“君子去仁,恶乎成名”、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”、“四十五十无闻焉,斯亦不足畏也”,这三句话都提到了要出名,“沽之哉!沽之哉!,我待贾者也”这句看到了孔子渴望被统治者赏识。只有出来做官,他的主张才能得以实践。这些都说明了他希望被人理解、被人重用。
然而他的仁政理想和屈原的美政理想一样,在当时都是一种乌托邦,多半是被当时的执政者所不理解的,所以,理想的幻灭,幻灭的孤独是不可避免的。
蒋勋在《孤独六讲》里谈到的“革命孤独”,我想这是孔子所经历的这种孤独。改革者所要改革的这个社会全都没有理解他,反而要驱逐他、迫害他,这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。这个时候什么会支持他走下去呢?
孔子感叹说:“知我者天乎”。这里的“天”能不能理解为一个更高的自我呢?孔子不语怪力乱神,所以我想把这个天理解为一个更高的自我,这个“我”在高处看护着跌在谷底的“我”,别人不能理解“我”,甚至嘲笑“我”,驱逐“我”,那么,怎么让这个“我”不碎成一片一片的呢?
这时候就需要一个稳定的“我”、一个更高的“我”做后盾,心理学上说世界都是自我投射的结果,我怎么看自己,我就怎么看世界,只要我还能理解自己,只要我还能坚定自己,那么,外界的冷言冷语只是一阵轻风,不足以动摇我理想的大厦。
前文提到了孔子的一些学生们都做了高官,但孔子在仕途上并没有很显赫的地位,其实这大部分也是他主动拒绝的结果。
比如卫灵公是想跟孔子请教军旅之事,孔子也是精通的,如果孔子投其所好,孔子怎么会不被重用呢?但如果孔子投其所好了,他就得放弃自己所追求的梦想,是要压抑理想获得重用还是要追求自我但遭受冷落呢?他选择了拒绝前者。即便被重用,但压抑理想扭曲自我依然是孤独的,而追求自我但遭受冷落也是孤独,同样都是孤独,但后者可以让真我得以释放,这就是孤独着且自由着。
还有一个例子也可以表现孔子的主动拒绝。
当时鲁国的卿大夫季氏在鲁国权势很盛,鲁国的政权都把握在季氏手里,而阳货是季氏的家臣,季氏的家政又被阳货把持着,所以,阳货在当时的鲁国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。
阳货曾经想请孔子出来做官,但孔子最恨的就是阳货这样的“乱臣贼子”,所以,不愿与其来往,更不愿意去他手下做官。阳货曾上门来拜访孔子,孔子都避而不见。后来阳货想出了一个办法:
送一头熟乳猪给孔子。孔子就不得不去见阳货了,为什么呢?
因为按照孔子所推崇的礼来说,别人送了礼就应该去回拜。但孔子实在不愿意见阳货,于是,叫他的弟子去打听阳货什么时候不在家,趁阳货不在家时去回拜。结果却在半路上遇到了阳货,孔子不得以只能敷衍他。
阳货问他:“自己身怀本领却任凭国家混乱,能叫做仁吗?”孔子说:“不能。“想做大事却总是不去把握机遇,能叫做明智吗?“不能。”“时光一天天过去,岁月不等人啊。”“好吧,我准备做官。”孔子虽然嘴上说他要去阳货手下做官,但实际上表面应付他而已,实则是拒绝他。
《时间的压力》这本书的作者夏立君谈到有被动的孤独和主动的孤独,他认为主动孤独的人是可贵的。“存在的孤独是必然的。区别在于是主动孤独还是被动孤独。人们体验到的孤独几乎全为“被动孤独”,是不得不孤独。”,“最伟大的文化创造,常由主动孤独者来完成。老子、庄子、司马迁、陶渊明、曹雪芹、鲁迅等,皆可视为主动孤独者。”孔子又何尝不是一个主动的孤独者呢?
孤独是客观存在的,但承受哪部分的孤独是可以选择的,他选择了追求仁德,并终其一生去宣扬它,为此承受了相应的孤独,这是一种有价值的孤独。
面对世人的不理解,他淡然一笑,《孔子世家》记载道:孔子适郑,与弟子相失,孔子独立郭东门。郑人或谓子贡曰:“东门有人,其颡似尧,其项类皋陶,其肩类子产,然自要以下不乃禹三寸,累累若丧家之狗。”子贡以实告孔子,孔子欣然笑曰:“形状,末也。而谓似丧家之狗,然哉!然哉!”
郑人说孔子看起来像丧家狗,孔子听了不但不生气,反而能自嘲一笑,欣然接受,这就是孔子对于自己坎坷处境的心胸,对于世人不理解的心胸,对于孤独痛苦的心胸,李白有诗:“空长灭征鸟,水阔无还舟”,孔子心阔似海,也许我们所谓的孤独和痛苦,在孔子宽广的心怀里,都能很快消弭于无形。在孤独面前,孔子是自由的。
面对世道混乱,无人重用,孔子选择发愤勤恳,努力学习,教书育人。孔子35岁到齐国寻求重用无果,后来回到鲁国,35岁后至50岁之前,就在家读书习礼,教书育人,晚年修订六经。
孔子既好仁也好学,他曾说:“好仁不好学,其蔽也愚”、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,做学问也是他人生中的大事,在无人理解不受重用的孤独岁月里,他用学习来充实自己。
进可问政,退可求道,孔子过着一种多维化的生活,让他在进退之间都有足够的空间,这样的空间给了他自由,使他能游刃有余,进退自如,孔子非常执着坚定地追求他的梦想,但他不偏执,不极端,我想正是这种多维化的生存方式给了他弹性和从容。
最后,做个总结:
生活中,我们常常把热闹和快乐联系在一起,把孤独和痛苦联系在一起,但真实的状况其实没这么单一,热闹有时也让人挺痛苦的,孤独也可以是自由而轻松的。最重要的是人自己心里有没有火光和方向。
孔子为追求仁政而颠沛流离,有很多痛苦的时刻,但他心里有一种对梦想很炽热的爱,这种东西是温暖的,这足以照亮他人生中那些黑暗时刻。有热爱,就是有归宿的;没有热爱,就是无家可归的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,我们还可以说孔子是孤独的吗?他只是表面看起来孤独,实际上他内心热气腾腾,不仅温暖了他自己,温暖了他的弟子们,更是温暖了千百年来后的人们,“天不生仲尼,万古如长夜”,诚哉斯言!
![]()

个人简介:郑燕璇,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砺青中学,青春语文名师工作室成员,追随青春语文,追求教育幸福。
![](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