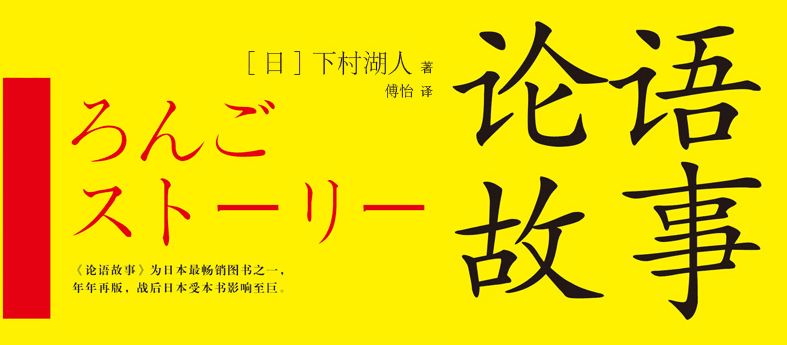
孔子与弟子:一以贯之
子曰:“参乎!吾道一以贯之。”
曾子曰:“唯。”
子出。
门人问曰:“何谓也?”
曾子曰:“夫子之道,忠恕而已矣。”
——论语·里仁篇
「眼见老师日渐衰老,真让人难过。」
「不是将近七十?」
「今年七十岁啦!」
「师母去世,是前年?」
「嗯。」
「哦!七十了。这两年来,夫子衰弱多了。」
「人到七十,总难免衰老。不过,他的心却越来越澄澈。」
「对啊,近来,每次和夫子在一起,都仿佛置身于水晶的宫殿里面,不知不觉之中,好像我的身体也变得像水晶一般透明了。」
「你能自我感觉像一块水晶,真是令人佩服之至。但是我怕在别人看来,你会显得像一块肮脏的小石头呢。」
「别开玩笑好不好?」
「我最近每到老师面前,都不禁肃然起敬哩。」
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?」
「那种感受很难表达,总之是一种发自心底的无可言喻的喜悦。」
几个年轻而活泼的弟子,正围聚在一处聊天。其中子游年纪最大,今年二十五岁;子舆、子柳两人都是二十四岁;更年轻的有子张、子贱、子喜与子循。在这群年轻人中间,子舆是很受大家尊重的一位,也是得到孔子喜爱的年轻弟子之一。子舆名曾参,外表看上去显得有些鲁钝,但实际上却内藏机智,是个善于反省的青年。比他大三岁的有若和大他两岁的子夏,在机智方面或许可以与他相敌,如果他们俩今天也在这里,谈话必定更加有趣。但今天这两人都不在。
在这些年轻的弟子看来,老师的智慧是深不可测的,他们能够领悟的仅仅是其中极微小的一部分。所以,对于那些不能领悟的,他们不得不常常借助于猜测和想像,而夫子本人也是他们说不完的话题。
「唔,不过老师近来沉默寡言,很少指导我们,大家说呢?」
「不见得,时常被老师责备的人也有啊,比如我就是其中之一。」
「你,当然要算做例外了。」
「胡说,就是你,不也时常被挖苦?」
「喂,喂,算了吧。别吵架好不好?······不过,他说得也对,近来老师变得寡言了。」
「嗯?我不认为这样。」
「不,的确比从前沉默多了。」
「老师向来就沉默寡言,并不是最近忽然变成这样的啊。」
「对了,前日有个很有趣的事。」
「有趣的事?关于老师?」
「嗯,他们也像你们一样,大概是对老师的沉默误会了,五六个人一起去老师那里抗议。」
「妙极了,怎么讲?」
「他们说,老师对有些人指导得很认真,对他们却一点也不理。」
「说得太没有礼貌了。」
「哪里没有礼貌,我们不是都有同感吗?」
「不一定大家都有同感。」
「好了,好了,让我们先听他讲完。那么老师怎么说呢?」
「那,用不着说。」
「喂,不要装聪明好不好,难道你能料到老师的回答?」
「不,我没有料想到。如果早就知道,绝对不会跟他们一同去抗议啊。」
「噢?原来你也去过!你为什么说用不着讲?」
「老实说,大家听完老师的话,只是一愣。」
「到底怎样?老师答些什么?」
「只要彻底了解老师平时的为人,是不难揣摩的。」
「喂、喂——还在装模作样,算了吧。」
「我哪里装模作样?原来你们也和我一样,还不能够真正了解老师,这倒让我有点放心了。」
「别欺负人好不好?」
「别生气,我告诉你们好了。······不过,难道曾参也不能揣摩得出来吗?」大家都转头望着曾参,可是曾参只是微笑着,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周围的同学,一声不吭地低下头。
「既然曾参也不知道,我就可以放心地说了。老师的回答是这样的——难道你们以为我还有什么知识不肯传授你们吗?我所追求的大道是没有任何秘密的,我不过在每时每刻都践行大道。你们希望接受我的教育,就应该从我日常的言行中学习。只在嘴巴上面讲的,不能算是道,虽然我不在口头上教正你们,但是我并没有隐瞒什么。你们把我这个名叫孔丘的人,当做这种人好了。——你们认为如何?是否也感到无话可说?」
大家一味默默地想着,只有曾参仍然面带微笑。
「后来大家怎样?」等了一会儿,一个学生问道
「我们都非常尴尬。大家只是沉默着,一句话也不敢说。」
「老师再没有说些什么吗?」
「嗯,有啊。他的声调非常沉痛,······原话我已经记不太清了,可是他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:言语本身是无力的,对于不肯主动探究真理的人,即使说尽千言万语,也不能使他获得教诲。所以,除非大家对于真理有强烈的探究心,因为求索而不能领悟,更加发愤努力时,我不会启发大家的。你们在还没有理解事物的道理以前,便想用高深的术语来表达它。可是,除非你们真正心有所悟,口欲言而不能,除非到了这种时候,我不会用言语来阐发的。当然,刚开始我会举出问题的一隅,让你们去研究,你们应该举一隅而反三,靠自己的心力去研究它。不到心求通而未得,不到口欲言而未能,我就不会用言词去教导他;举一隅,不以三隅反,我再不会更进一步教导你们哩。——就是,老师的话大概就是这样。」
「噢,这才了解老师的意思啦。」
「这样说来,平常被老师指责的人和不被老师提到的人,该是颇有悟性了。」
「不过还要看被指责的性质。」
「那当然啦。……那么抗议团就这样回去了?」
「不是只好这样吗?」
「太没面子了。如果我和你们一起,至少还要说几句。」
「嘿!伟大伟大,让我们听听。」
大家都好奇地等着那位同学发表高见,连曾参也睁大了眼睛。
「我们知道,老师的教育精神是注重实际,对于某一些人,老师常给予谆谆教诲,而对于另外一些人却不加过问。这些我们也大致猜得出他的理由。可是,老师对弟子们提的同一个问题,他的解答往往因人而异,这我们就不能理解了!」
「那有什么奇怪,提问的学生,资质有高低之别嘛。」
大家的情绪不像刚才那样紧张了,他们的谈话轻松了许多。
「根据资质的高低,回以详简不同的解答,这一点我自然懂得。不过,老帅的解答有时互相矛盾哩。」
「譬如,什么事?」
「有人曾问老师:『领悟了道理之后,是否马上就去实行它?』老师回答说:『不可以,应该和父母兄弟商量之后才可以去做。』但是在别的场合,另一个人问同样的问题时,他却肯定地说:『当然,你应该立刻去实行。』」
「是谁?谁问这事?」
「我也不大清楚,听说是前辈子路和冉有,公西华听到后,曾经对我说,他要就这件事质询老师。如果有机会,我也想问老师。」
「我想,这也是老师因为子路和冉有的性格不同,而给予不同的教诲。」
「或许是吧。可是,按照个性教育学生也该有个限度,老师对学生的教育如果变动不定,没有一个根本的准则,那就会使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。本来,我们跟随老师求学的目的,在于探求恒定不移的道理。如果这个道理会因为父母兄弟的意见而变动,那能算是永久的道理吗?我们来学习不是为了求取不可靠的东西,我们需要的是超越任何时间、空间与人为因素,适用于任何人的普遍的真理。」
「赞成!赞成!」几个学生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。
其中有一个学生,首先观察了一下众人的神色,然后说道:「这样看来,我们所学到的,不过是零碎的末道小技。」
「末道小技,这样说未免过分。」
「不过,我们所学到的道德知识,不是非常多吗?」
「勉强可以,不过,都是零零碎碎的。」
「无论是零碎的或是没有系统的,孔子的教学确实因人而异。」
「曾参,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,你意见如何?」
曾参一直听着,虽然不吭声,可是在内心里,对同学过分浅薄的态度,他却暗自感到痛心。当同学询问他时,他很想说明自己的观点。但是考虑到自己虽然可以打消他们的牢骚,但是不敢保证能使他们口服心服。在这种情况下,擅加评论反而有违老师的训诫。并且,他也很想知道,善于击中问题要害的老师,在这种情况下,会如何去教诲他们。——这样想着,他委婉地答道:「老师快要来了。这么重要的问题,让我们直接请教老师怎样?」
「当然也要问老师。不过,你有什么意见,我们也希望听听。」
同学的话里,流露出挖苦的味道。可是曾参置之不理,干脆地答道:「不,我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意见。」
大家仍旧围绕着这个问题唠叨不休,不过,始终没有一个人言中问题的核心。他们甚至肆无忌惮地说些冒渎的话,曾参认为这太过分了。他想,如果这种情势有增无减,他将不得不表明自己的见解,以便结束这种可耻的讨论。
非常巧的是,正在这时孔子走过来了。
「好热闹呀!」孔子这样说着,穿过恭恭敬敬起身迎接他的弟子,来到当中的席位坐下。最年长的子游,代表大家向孔子鞠躬致礼之后,又把刚才讨论的问题,客客气气地报告给孔子。
孔子的眼神像秋水一般澄澈。他听完子游的话,好像点名似的,拿目光扫视过每个弟子的脸,最后将目光停留在曾参脸上,静静地,可是严厉地说道:「曾参,吾道一以贯之。」
曾参恭恭敬敬地俯首点头,确信不疑地回答:「是的。」
这时候,孔子忽然离开座位,留下那些由于惊奇而面面相觑的学生,迈着平稳的步子走了。
久久地,大家像中了魔似的,无言地呆坐着。曾参在孔子离去后沉思了一会儿,然后向同学们点了点头,站起身来。
看到曾参要走,大家回过神来,赶紧把他拉住了。
「刚才到底是什么意思?」有一个人说。
「只是说一以贯之,根本使人觉得莫名其妙。」另一人说。
「曾参,我看你回答老师的时候很有自信呢。你真的了解吗?」又有人不服气地说。
大家围住曾参,急切地向他索要答案。
曾参环视了一下左右,静静地答道:「夫子之道,忠恕而已矣!就是说:尽己谓之忠;推己及人谓之恕。」
听了他的话,大家犹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。曾子申述道:「你们刚才一直胡说乱扯,说老师的教育是末道小技,是零碎杂乱的,或者对个人有偏差等等冒渎的话。可是诸位如果仔细想想,你们一定会发现,这些都是一贯的圣道的具体表现哩。老师并不向我们灌输抽象的圣道,而是借具体的、现实的事物教育我们,启导我们。因此,表面看仿佛是片段的零碎的,或者对个人有偏差,但依我的经验看来,即使片言只语,夫子的教诲无不源于圣道。最近,我越来越发觉这一件事实,日日为之倍加惊叹。我越加以思索分析,越清楚地看到,老师一切的言行都密切地秉承圣道,始终一贯而不渝,小至日常起居等琐事,大至救国救民的大事,无不贯通如一,丝毫不差。」
大家一言不发地听着,似乎渐渐有所领悟,不由自主地点着头。可是曾参仍旧很不放心,继续强调说:「但是,老师的言行能够始终一贯,并非他的聪明使然。单凭思维缜密,绝不能保证他的言行丝毫不渝。在老师看来,道理并不是理论,而是发自衷心的愿望,是生命历经艰苦磨琢所得到的一种结晶,没有它,夫子便不能感到生存的意义,也不能体会到生活的乐趣。因此,圣道的一贯,无需任何理论说明,它是孕育于自然的浑然贯通。」
说到这里,曾参不觉吃了一惊:他发现,不知不觉地,自己正在用讲道的口气,教训着他的同学呢。立刻,他的脸上涌起一阵羞红,逃窜似的溜走了。
大家茫然地望着他的背影。他们像是了解,又像是不了解似的,呆呆地僵立了一会儿,然后纷纷地四散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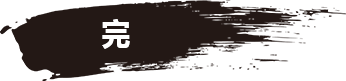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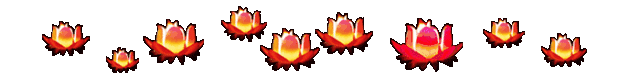
〖 归悟生命之源 · 承传文化之美 〗
微信公众平台:素华生活馆
电话联系:18320181526
欢迎扫描二维码关注:

「 素品人生:素口、素心、素行、素文明 」
致谢声明:所有资讯仅供学习研究之用,版权属原作者所有。如作者不便转载,敬请告知,我们会迅速回应与删除。